
在过去,“互联网大厂中层管理者” 的身份有一圈自带的光环,它意味着当下的成就和远处确定的未来:相比其他行业,他们年龄往往更小,却有更大的管理权限,每一次决策都有机会影响公司乃至行业;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里,升职加薪的机会更多,如果幸运一点,能陪伴一家企业敲钟上市,他们也更容易实现财富自由;即便在正常的发展路径上,他们的年薪和股票也足以跑赢大多数同龄人。
这是另一种意义的 “上岸”,也因此,他们在消费和投资上更愿意付出真金白银,比如孩子的教育和高杠杆买房。但现在,河水再度湍急起来,在行业急剧变动中,互联网大厂中层成了一个尴尬的身份,业务紧缩,他们的升职通道关闭,本身也不如年轻人那么有性价比,被辞退的危险更大。
靠不断加班、自我抽打就可以获得升职的岁月也一去不复返了。更多的是要看业务、行业是否符合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,与个人意志和能力无关。
而一旦离开,他们就面临着更严峻的现实问题:没有更好的出路,上有老下有小,背着房贷和车贷,他们只能接受降职降薪,生活水平、自我认知上也出现了巨大的落差。
中层们夹在中间,左右为难。
“12 点到了”
做了十几年在线教育行业,林森最终坐在了一家传统光伏企业的业务主管对面,从简历开始接受审视。这滋味并不好受。
没有寒暄,对方看了他在高途的履历后直入主题:“你是被裁员了?” 他没有解释,只是给出肯定的答案。对方的质疑接踵而来:“按理说,教育行业永远不会过时,你这时候被裁员是不是个人能力有什么问题?”
听到这个问题,林森基本知道了面试结果,他固然生气,可作为一个上有老、下有小,房贷车贷齐备的求职者,他没法拂袖而去。他劝自己:说不定这是压力面试,再忍一忍。
对方的下一个问题浇灭了他最后一点侥幸。面试官开始质疑他履历的真实性。对方说正好有一个朋友也在高途,却没听说过有这个岗位和林森这个人。林森被一连串攻击性问题问得发懵,依然努力保持正常的沟通节奏,确认了面试官这位朋友的姓名之后,林森知道自己没有这位同事。
这个全程仅有 5 分钟的面试结束了。“这个业务主管并不了解在线教育,最后 HR 反馈,我和这个岗位需求不匹配。”
过去一年里,有许多和林森一样的互联网中层管理者,出于各种理由重新流入人才市场,接受企业更为严格的审视。
李楠在某大厂做了 8 年的产品经理,以前常有猎头主动打给他。被裁员后的最近一次面试,业务主管说他各个方面能力都不错,但就是迟迟没有下一轮面试的消息。其他市面上类似体量的公司 “不裁员就不错了,headcount 早就锁了”。
以前字节跳动是李楠所在大厂的员工比较喜欢的一个下家。作为行业内发展势头最好、业务扩张最快的公司,字节跳动曾经一年内招聘 4 万人,今年也踩了急刹车。就在本月,字节跳动 CEO 梁汝波更新个人 OKR,表示将大幅降低 2022 年~2023 年招聘计划,把降低组织规模增速、提升效率作为重要指标。
离开大厂的中层们,普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好找下家。

▲ 图 / 视觉中国
“今年的就业市场相对去年有比较明显的供大于求。有很多互联网中层在看机会,大部分都是在 P8(同等)的职级。”CGL 高级合伙人 Jason Han 说,“但实际上很多企业不太愿意接纳中层的加入,反而 P6(同等)更好找,因为对新环境的融入度高、入职的预期也相对较低。”
今年 1 月~4 月,猎聘大数据追踪程序员的投递行为发现,在有跳槽意愿的求职者中,愿降薪跳槽的人占到整体大厂技术求职者的 55.34%,超过一半。在不同职级的互联网大厂人中,中层大厂人今年 3~4 月愿意降薪跳槽的人同比增长最多,为 25.74%,比去年同期增长翻倍。
进入买方市场之后,中层们的预期也不得不随之调整,优先解决现实层面的问题。
林森最终入职了腾讯的信息安全部门。在面试时,他依然感受到面试官对自己能力的不信任。“直接把职级压成主管,年薪降了起码 30%。” 但林森也可以理解,“这个岗位倾向于有呼叫中心和客服中心工作经验的人,找我纯属是因为在线教育行业一下出来了太多人。” 佐证是,一个曾供职于新东方的总监,现在也成了他的同事。
除此之外,林森还要面对管理带宽、工作内容的落差。从管理 150 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,到亲自和一线人员沟通,做一些更接近体力劳动的工作。但他算了一笔账,“我一个月房贷 4500 元、车贷 6500 元,女儿每个月的早教、生活费也要 3000 元,我还能躺在家里等机会找我吗?”
Jason 现在也会建议中层候选人 “降低预期”。在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下,企业、招聘方的选择多了,更需要专业和行业背景同时适配的人。“我会让候选人列一下自己的技术能力最适配的场景。比如在线教育的技术中层,他的技术优势切换到电商、社交就需要进行重新匹配。候选人也能理解这点,同时会明白这意味着年薪要打折扣,现在中层转行的降幅普遍在 20% 左右。”
阿里前员工张敏是那种认为自己不会离开杭州西溪园区的人,但是她说:“过去的很多年,我们很多人都像坐上了南瓜马车的灰姑娘,我们以为这场盛会永不会结束。但现在,12 点到了。”
“认清现实,放弃幻想”
中层管理者们的简历充满着 “成了” 的瞬间。林森亲自参与了高途区域运营中心从无到有的全过程,团队在半年之内完成超过 5000 万营收;一位前视频网站的市场负责人简历上写着超过 10 年从业经验,一连串耳熟能详的爆款项目,站内热度、曝光量、招商情况一应俱全。
这些履历上覆盖着一层柔光,显示了过去黄金 10 年,移动互联网浪潮下,一些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如何一步步成长为大型企业的中流砥柱。他们通常在 35 岁左右,毕业于 985/211 院校,有远见、魄力来到互联网企业,并且有能力借助大势将业务做成。
在此前,他们只要把握住公司上升的势头,OKR 必达,或是跟对老板、接触到核心业务,升职加薪之路就会十分顺利。“只要你负责业务的增速高于公司市值(估值)的增速,没拖团队后腿,在大厂的评价体系里你就是合格的。”Jason 说。从带几个人的团队到带上百人的团队,他们成为企业重要的中间层、各个业务线沟通的桥梁。
他们对工作评判标准也依赖过往的成功经验。最近从阿里离职的一位中层说,评价新岗位的 “含金量” 要看是否是企业核心主营业务、是否还有持续增长的可能。
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很多感性因素,比如个人自尊心。发现面试官是自己曾经的下属,想也不想就可以立刻放弃这个机会,“也省得对方尴尬”。而直到 2021 年上半年,就业市场都可以宽容这种 “任性”—— 毕竟跳槽涨薪 30% 根本不值一提,总包翻倍才是行业 “正常水平”。
但现在,整个行业都在 “降本增效”,具体点说,互联网公司更加聚焦那些赚钱的业务,烧钱扩张的业务基本不做了,战争都不打了,谁还愿意开出涨幅 30% 的高薪去挖人呢?
“职场就像名利场。成功的时候,所有人都可以看见你,聚光灯打在你身上。但当你(你的公司 / 行业)处于下风的时候,没有人会再过多关注,这是职场很现实、残酷的地方。”Jason 说。
许多大厂中层在降低自我预期之前,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 “成功”。

▲ 中关村软件园,是许多大厂中层辉煌的起点。图 / 视觉中国
林森见证且参与了整个高途运营中心从 30 人到 200 人的规模增长,晚上 12 点下班之后,他躺在床上仍在在想哪些工作需要立刻布置、哪些关键指标需要跟进结果,每天复盘 2 个小时之后,才能安心休息。
“我全部心思都在工作、都在学生身上。” 他对这样的工作强度毫无怨言,甚至直接劝退了一个下班后就不再回复工作信息的老师。“我们要求学生的消息 2 小时内必须回复。”
林森成了学生最信任的那种老师,也获得了同行业顶尖的回报和更广阔的可能性,代价是付出自己全部的时间。在线教育风口的那两年,连他的下属跳槽到 BAT 都能直接晋升到经理的级别。但是,行业震荡之后,留在高途的林森也一同坠落,而那位跳槽到大厂的同事,现在的职级远高于他。
“选择、时机大于努力”,林森这样安慰自己,既然享受了前期行业的红利,就得承担现在这个选择带来的结果。“教育行业在风口上的时候,可能我们从业者的薪酬水平极速提升了,而能力并不匹配。” 他这样反思。
“选错行业就会很难。比如曾经做过 P2P 行业的人,他们的简历里如果还保留这段经历,会对职业履历大打折扣。”Jason 说,“有些人宁可‘开天窗’,说出国旅行了、结婚生子了,也不想再提这段经历。”
在阿里工作了 6 年的尹默是一位 P8,她本来以为阿里内部赛马的竞争强度已经足够激烈,任何一个团队想要获得集团的资源都需要拿出能说服人的结果。即便同属一个 P9 管理,两个团队想要获得阿里妈妈的资源倾斜都需要内部比稿,不论输赢,双方都需要给资源方写复盘总结,“清晰说出我的方案到底强在哪里”。
凭借一次次的比稿、IP 打造,尹默可以完成上亿的成交,和很多头部企业高管平起平坐。一开始她不理解为什么有中层员工在阿里供职超过十年,当她离开阿里,发现自己已经不太理解 “娃圈”“谷圈”(动漫周边)是什么意思,才明白为什么很多阿里中层不愿意离开。
“其他公司接不住一百万左右的年薪只是一个方面,另一面是我们对平台有路径依赖。说白了,阿里的试错空间很大,我们不用对一个营销方案的结果 100% 负责。”
很多人会用 “在电梯里做俯卧撑” 来比喻中层们不堪一击的优越感,意思是坐上一部上升的电梯,不管用什么姿势都能到达顶层。“很多中层只是跟对了人、选对了业务、有执行力,而不是真的有创造力。”Jason 说。
一位猎头告诉坦言,这一拨大厂出来的中层管理者很难在同级别的公司找到 “合适” 的岗位了。“还是要认清现实,放弃幻想。”

▲ 图 / 视觉中国
最低限度的生活
离开大厂后,曾经意气风发的中层们,不得不适应新的现实。
李楠在 31 岁的时候加入某大厂,如今已经 39 岁,去年年底,他所在的房地产业务条线被整体裁撤,给了 N+1 的补偿,但股票不会兑现。他决定发起劳动仲裁,从 HR、法务到副总裁都半劝半威胁地让李楠多拿几万块钱的赔偿,不要等公司单方面解除合同。但李楠不愿意。“我人生有 8 年的时间都投进这家公司,但最终,他们这样对我。如果我同意协商,可能这辈子都觉得恶心。”
但为尊严而战要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 —— 仲裁的 1~2 年之间,李楠不能有任何社保记录,无法入职新的公司。“社保断了就断了,我反正没想拿北京户口。” 他说,“房贷每月一万五,我还可以用积蓄撑一撑。”
李楠愤愤不平的,是自己在公司的 8 年,一直像一个不断跑动的补位者,总是在不同的新业务之间流转,“一个新业务,很着急说要做,刚刚有点起色,又很快不做了”。
在这种反复跑动中,李楠的个人能力和成绩变得难以评价。除了大范围普调和一次升职之外,他没有获得任何职业上的成就感。李楠想过离开,但最终看看每年普调的薪酬、每年按月份分别到期的股票,他又按下了这个念头,想着就把公司当成 “领工资的地方”,这样撑过了 8 年。中间也有猎头带着字节跳动薪酬涨幅不错的职位找来,他想也不想直接拒绝,背后是互联网追捧年轻人给他带来的自卑感。“字节都是年轻人在‘卷’,我岁数大了,也没有那个自信了。”

▲ 字节跳动的员工大多非常年轻。图 / 视觉中国
离开老东家之后,李楠开始专心拍起抖音。每一天都过得极快,找选题、写稿、拍摄、发布,自己再做两顿饭,一天就过去了。很多时候李楠起床说的第一句话,就是对着镜头。
成为一个自媒体从业者,让他脱离了大厂产品经理的惯性,进入了碎片化的生活。每时每刻都有人找他,境遇相同的同事会来问候、关注者会来咨询裁员赔偿的流程,甚至还有粉丝让他帮忙修电脑。
最近他的选题是拍摄自己如何用 1000 元生活费(刨除房贷)在北京生活:一日三餐都自己下厨,青菜面条为主,周末能吃点肉,一个月伙食费最多用掉 800 元。偶尔改善生活,在附近的批发市场买一买应季水果。算上交通费、宽带费,满打满算每月的基本生活支出是 1600 元左右。这是一个人活下去最基本的开销。
除此之外,他还有各种省钱妙招。比如给购物软件多建几层文件夹,降低平时打开的频率;再把银行的 App 放在屏幕最显眼的位置上敦促自己攒钱,线下购物也直进直出,只买必需品;最后善用记账软件,时时回顾自己的开销。
即便是中国人最重视的新房家具,他都买二手的。衣柜是在二手市场淘来的,800 元一个,不仅送货上门还帮他修改了尺寸;餐桌、餐椅、电视柜一整套全买下来只要 2000 元。有人嫌弃二手家具太脏,李楠平和地给出他的解决方案:“用抹布蘸点白醋,一擦就掉了。”
他反复说,节省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,不是因为裁员失业。“人不要对物质过度追求。” 在片尾他还反问,“那些一个月就花掉五六千的人,都是把钱花在哪儿了?”
在消费主义席卷中,有一句很蛊惑人心的话:每一笔消费,都是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。按照这个标准,李楠在北京过着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。一个月一万五千元的房贷正好是妻子一个月的收入,优先保供之后,一家三口的生活费、儿子的学费和住宿费都成了问题。
视频里,李楠看上去随遇而安,接受了自己的处境。只有偶尔和粉丝聊天的时候,才会暴露自己的脆弱。“很多人质疑我的开销,然后我才发现,原来我在北京没有生活。没有娱乐活动和人情来往、没有聚会、没有份子钱。” 他说,“其实还是家乡好,有父母亲人,还有家乡美食和空气里独有的味道。” 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,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,“还得挣钱”。“在北京总是有一种焦虑感,趋使着自己要干点什么,不能放松。”
他最近开始尝试在线上线下接一些广告。“有个前同事在做 MCN,他们帮我接商单。具体的合作细节都是他们聊。” 目前为止拼多多、转转都投放了他,原本拼多多希望他能推广 iPhone 13,但李楠觉得自己买不起,把产品换成了自热小火锅。他刚给一个招聘网站拍了视频,拿到 1000 元劳务费,开开心心给自己买了肉吃。有人以为在抖音卖货可以挣到大钱,他解释 “总共挣了大几百,后面没有‘万’字”。很多粉丝看到他的境遇心有戚戚:李楠现在做的事情,就是未来我们 40 岁被大厂裁员之后能做的事,哥先给我们打个样了。

▲ 更年轻的员工们走进腾讯大厦。图 / 视觉中国
还有一些更惨的故事:腾讯有中层申请了公司福利中的购房无息贷款,结果被裁员了,要返还几十万的贷款,对于掏空积蓄买房的大厂人,这得是多大的压力。
只有像尹默这样没有牵挂的中年人才能感到轻松,她没有结婚,没有房贷,离开阿里之后,去了很多地方旅行。她看见成群结队的马匹、走过汇聚中的雪山融水、感受到 26 度的山风从崖底吹来。
太阳终究会落山的,也许,其他地方的夕阳更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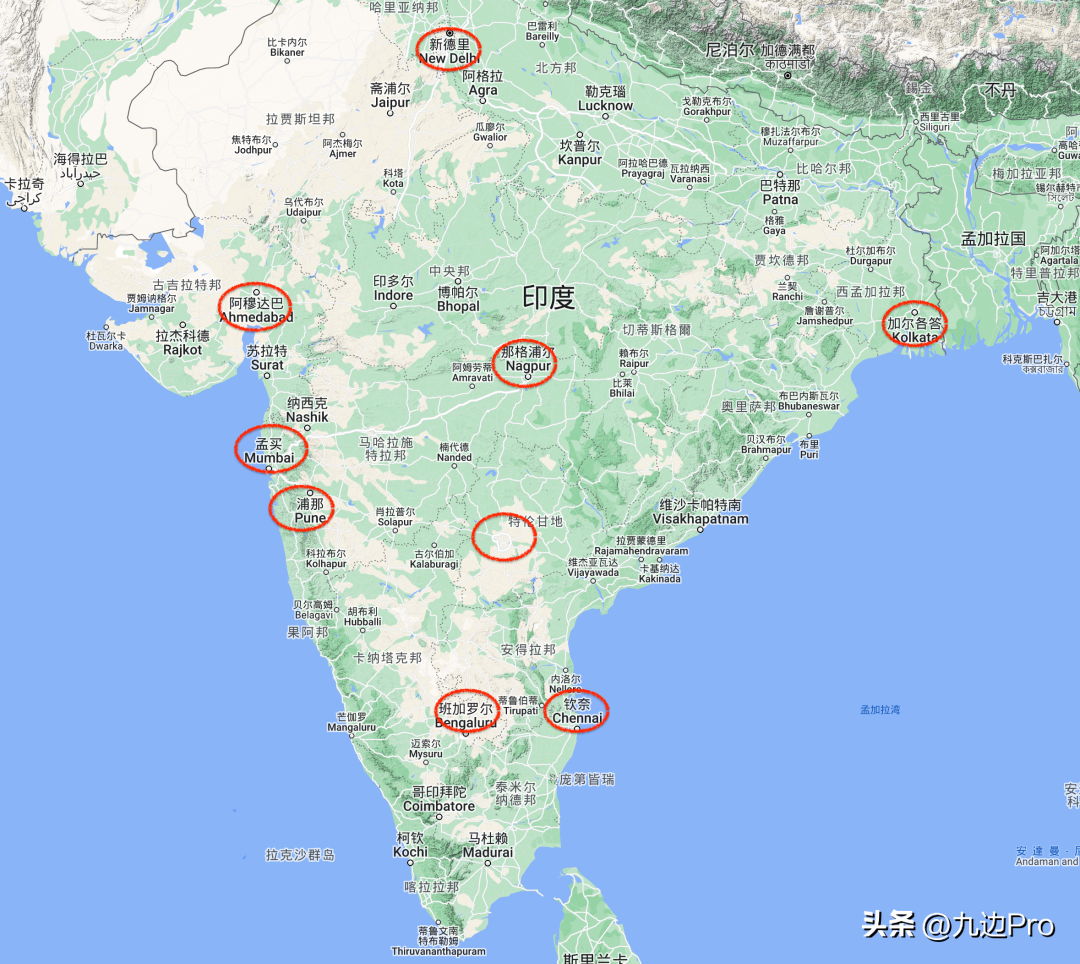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太阳终究会落山的